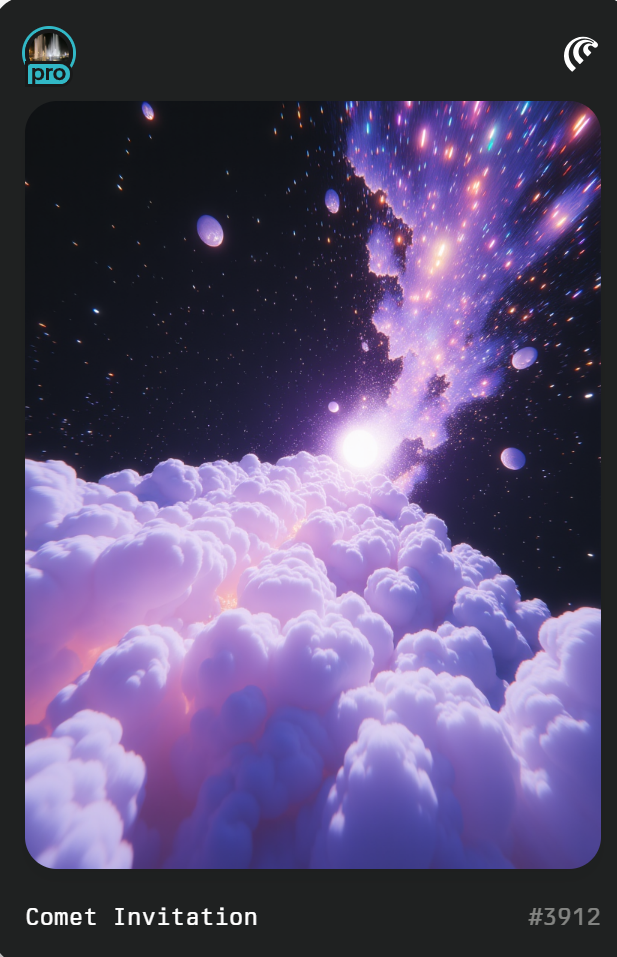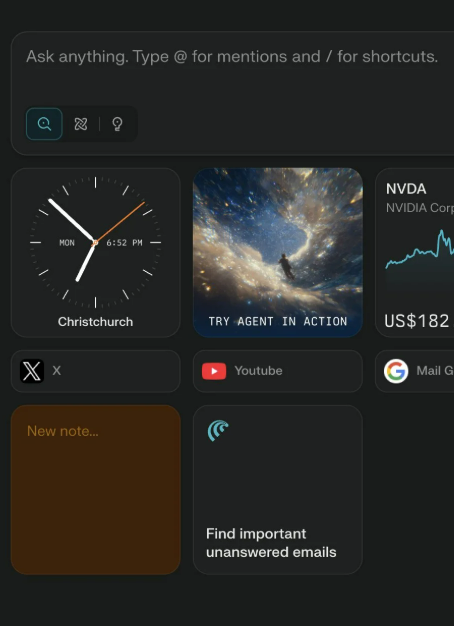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知识铺
陈永伟/文 当地时间3月27日,普林斯顿大学发布讣告,称该校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的荣休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于当天去世,享年90岁。
卡尼曼将自己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作为心理学家,他在认知心理学和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但作为一名学者,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学方面,其影响尤为巨大。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如日中天,经济学家们正狂热地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去“殖民”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则反其道而行之,愣是和几位合作者一起用心理学理论对经济学实施了一把“逆向殖民”,并成功地创立了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2002年,他因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卡尼曼之前,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是以理性人假设作为出发点的。正是卡尼曼和其合作者的工作,才让“非理性”成为了这个学科的研究主题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学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而这个领域的几个最重要理论几乎都可以在卡尼曼那儿找到渊源。
早年岁月
1934年3月5日,卡尼曼出生于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特拉维夫市。卡尼曼的父母都是从立陶宛移民到法国的犹太人,平时居住在巴黎。当时,他的母亲正好去特拉维夫探亲,而这个犹太小生命恰巧就在犹太人的故土降生了。
卡尼曼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的父亲以法莲·卡尼曼曾在欧莱雅公司(L’Oréal)担任研究主管。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在纳粹的搜捕中,以法莲被投进了集中营,但在雇主的斡旋下得以侥幸被释。之后,以法莲带着全家逃亡,并在法国中部暂住了下来。1944年,罹患糖尿病的以法莲因缺医少药去世。几周之后,盟军发动了诺曼底登陆,法国亦在不久之后全面光复。
1946年,卡尼曼随母亲搬到了他的出生地特拉维夫。在那里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但两年后,随着以色列建国,他又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并再次在炮火纷飞中历经生死。直到十个月后战争结束,生活才重新稳定下来。虽然在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后,卡尼曼终于拥有了祖国,但他一直很难融入这个新的国家。他虽然很快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家里却一直说法语。他不太愿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而更愿意像个学究一样读书思考。
在移居特拉维夫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了心理学上。按卡尼曼自己的回忆,他想要借此去弄明白是非对错在人们心中的起源。1951年,卡尼曼高中毕业进入希伯来大学,选择了心理学专业。当时心理学有两个主要流派: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和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但卡尼曼对这两者都不甚满意。一方面,卡尼曼很排斥弗洛伊德的那套通过挖掘童年阴影来解释心理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他也对斯金纳那样穿着白大褂、变着法儿折磨小白鼠的研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类研究完全忽略了对人类行为的关心。相比之下,他更痴迷于格式塔学派。他关心的是人脑是如何将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图像,而社会因素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另外,他也对神经科学感兴趣,甚至一度想成为一名神经学医生。
1954年,卡尼曼大学毕业以少尉军衔开始服兵役。进入军队后不久他就凭借专业知识调任以色列国防军心理部门,负责对新兵进行面试,并考察他们该被分配到什么岗位。起初,卡尼曼的面试主要靠直觉。但他很快发现,这样的结果很不准。按照后来他的学术术语,这是受到了“有效性幻觉”(illusion of validity)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个干扰,他编制了一个新兵的面试量表,从多个维度来评估新兵的能力。这份量表被以色列军队沿用了几十年。
1956年,卡尼曼结束了军旅生涯。希伯来大学学术委员会决定资助其出国继续深造。但当时的卡尼曼深感自己基础知识不足,于是先留在以色列自学了一年多。1958年,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在伯克利,卡尼曼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不过他读博期间最重要的智力收获并非来自研究生院,而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镇的奥斯汀·里格斯(Austen Riggs)诊所。1958年夏天,卡尼曼在那里学习了几个月。和大卫·拉波特(David Rapaport)等专家的交流启发了他,关于注意力资源分配的思考,以及分析“事后诸葛亮”(Hindsight Bias)行为的最初灵感。
初入学界
1961年从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后,卡尼曼回到希伯来大学任教,正式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卡尼曼的研究一开始集中在视觉感知和注意力方面。他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视觉实验室。
1965年,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卡尼曼选择再赴美国,在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和一位叫杰克逊·比蒂(Jackson Beatty)的研究生一起考察了人在催眠状态下被要求复述数字时瞳孔的变化状况。他们发现,人在听到数字时,瞳孔会稳定扩张,而在复述数字时瞳孔则会稳定收缩,这表明在短期记忆任务中,瞳孔收缩可以被用来作为考察人脑处理状态的指标。这个成果很快就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并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结束博士后工作后,卡尼曼向希伯来大学请求终身教职,希伯来大学对此不置可否。卡尼曼一怒之下决定先不回以色列,而是前往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的日子让他收获良多。除了获得很多研究灵感,他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结识了英国心理学家安妮·特莱斯曼(Anne Treisman)。12年后,她成为了卡尼曼的第二任妻子。
离开哈佛后,卡尼曼又到剑桥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1967年秋,希伯来大学终于同意授予卡尼曼终身教职,于是他放下对母校的心结,回到了以色列。
特沃斯基
1969年,卡尼曼邀请自己的年轻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来自己的研讨班作报告。特沃斯基是一位数理心理学家。两人虽曾同处密歇根大学,在研讨班上,特沃斯基报告了自己在密歇根的导师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的一项实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把两个装满了红白两色筹码的袋子放在被试(Subject,实验对象)面前,其中的一个袋子里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75%和25%,另一只则正好相反,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25%和75%。被试被要求从中任选一个袋子,并从中一个个往外拿筹码。每拿一个筹码,就需要向研究人员汇报一次他认为袋子里究竟是红筹码多还是白筹码多。
特沃斯基报告说,实验中被试的猜测会根据抽出筹码的颜色而不断调整,其行为模式大致符合贝叶斯统计的原理。但卡尼曼则对此表示了怀疑。在他看来,人脑在思考时并不会自发地参考什么数学公式,而是会更多依靠直觉。特沃斯基面对挑战不甘示弱,于是两人就在课堂上争辩了起来。所谓不打不相识,这场学术争论竟意外地让素来沉默孤傲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成为了挚友。
此后两人开始了长期合作。短短几年内,他们就共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并提出了包括启发性偏见、前景理论、框架效应在内的一系列重磅理论。
这些学术成就让两人在学术界声名大噪。前途更为广阔的北美学术界也为他们敞开大门。两人于1970年代相约共赴美国。由于学校招聘政策限制,最终只有特沃斯基受聘于斯坦福,而卡尼曼则去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尽管分属两地,两人还一直合写文章。只不过合作模式却变成了其中一人完成大部分工作,再让另一个人提出一些意见,最后两人合署姓名。两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了特沃斯基去世。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早在他们赴美之前就已获得经济学界的注意。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邀请他们作为心理学界的代表参与学术交流。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要说服主流经济学家采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困难。特沃斯基于是向卡尼曼建议,不如花心思去着力培养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下一代经济学家们。很快,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成为了他们的合作者与拥趸。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行为经济学创始人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以及弗洛伊德的外曾孙乔治·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等。
在这些后起之秀的努力之下,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终于进入经济学界主流。现在,大约每十篇经济学论文中,就有一篇属于行为经济方向。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以心理学家的身份,成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并于2002年斩获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遗憾的是,彼时特沃斯基已经因癌症去世,无法与卡尼曼共同分享这份殊荣。
在经济学家们接受了卡尼曼的理论之后,他们又将这套理论扩展到了其他的学科。这使得他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散。比方说,受塞勒的影响,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成为行为经济理论的拥趸。桑斯坦后来成为法学界的巨擘,并担任奥巴马政府的重要顾问,他和塞勒一起,将行为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制定,形成了著名的“助推”(nudge)理论,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卡尼曼的学术贡献
纵观卡尼曼的一生,其涉猎十分广泛,学术贡献遍及多个领域,发表的论文多达数百篇,因此要全面介绍其学术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限于篇幅,这里只着重介绍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几个开创性贡献。
一,启发性偏见
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人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情况时,人们会按照概率论公式进行决策。在卡尼曼看来,这个假设并不能充分刻画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在他还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时,就对此有所认识。他发现人完全不会根据数据和概率论原则去考察一个新兵适合干什么,而是直接依据直观感受做出判断。在卡尼曼终于用自己的观点说服特沃斯基后,两人将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了一套理论,即所谓的“启发偏见”(Heuristic Bias)理论。
在1974年的论文《不确定下的判断:启发和偏见》(Judgment 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biases)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首次阐述了这个理论。他们指出:“在面临不确定时,人们通常会依靠数量有限的启发式原理,这些原理将评估概率和预测值的复杂任务简化为更简单的判断操作。”
根据启发来源的不同,启发性偏差可以分为很多种:
首先,这种偏差的第一类是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给予过高的重视。比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要求被试根据对一个虚拟人物的描述来猜测他的职业。根据他们的描述,这个人“非常害羞和孤僻,总是乐于助人,但对人或现实世界几乎没有兴趣。他是一个温顺整洁的灵魂,需要秩序和结构,对细节情有独钟。”在描述完上述特征后,他们问被试这个人更可能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还是一个农民。虽然在这段描述中并没有包含任何关于职业的信息,但结果大多数被试都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一位图书馆管理员。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还发现,代表性启发偏见可能让人们无视额外信息和统计规律。在实验中,他们在向被试描述完虚拟人特征后,还额外给被试提供了这个人所在的社区职业构成信息,如“这个社区有70%的农民”。然而,实验显示,这些额外信息对被试的判断影响很小。
第二类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由于人的知识和思维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决策中,他们会更倾向于根据自己更容易获取的信息作为参考。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曾在一个实验中问被试:“如果从英文文本中随机选择一个词,那么它以K开头的概率和它的第三个字母是K的概率哪一个更高?”结果显示,被试们明显倾向于认为以K开头的概率更高。事实上,在常见文本中,第三个字母是K的单词概率要比K开头的单词概率高两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人们想起K开头的单词相对容易,从而想当然地认为它的概率更高。
第三类是调整型启发(Adjustment Heuristic)或者“锚定”(Anchoring)。这种启发性偏见指的是人们在进行估算和判断时,会更倾向于在一个“锚点”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整,即使这个锚点未必和问题有关。比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先要求被试估算非洲究竟有多少国家。然后,他们要求被试转动一个标有0-100的数字转盘,得到一个数值,并问他们认为自己估算的非洲国家数是比这个数值大还是小。随后,他们继续要求被试估计联合国成员里有多少个非洲国家。很显然,联合国里面有多少非洲国家是完全和转盘得到的数字无关的,但在实验中,被试对前者的估算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他转到的数字是10,那么他们报出的估算值平均为25;而如果他转到的数字是25,则报出的估算值平均为45.8。
在很多时候,这种启发式的决策方法是十分实用的,这可以大幅减少人们的决策成本。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决策方式却会造成很多问题。一类典型的问题是“过分自信”(Overconfident)。在实践当中,人们经常会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及某些片面的信息认定某事很容易处理。而这种草率可能会让他们陷于失败的境地。另一类典型问题是“事后诸葛亮”(Hindsight Bias)。它指的是人们在事后总是会根据直觉或某些信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事前就已预测到了事件的结果。比如,在某些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总会有人说事故的原因是很显然的,本来可以避免。但实际上,如果放在事前,这些事故原因未必就很容易被发现。因而,“事后诸葛亮”效应很容易造成对事故的错误归因与归责。
二,前景理论
在行为经济学兴起之前,经济学倾向于用期望效用理论来分析人在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分别计算每一种可能状态下可能得到的效用值,与相应状态发生的概率相乘得到加总的期望效用。
现实中,人们对于风险的倾向是不同的,有的人偏好风险,而有的人则回避风险。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期望效用大于收益期望值所带来的效用,那么他就是风险偏好的;反之,他就是风险回避的。
在很多情况下,期望效用理论都可以很好地预测人们的行为,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存在着问题。比如,人们其实会在不同的状态下,对风险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曾设计过一个实验,他首先让100个被试在A、B两个赌局中进行选择。在A赌局中,他们100%能得到100万元;而在B赌局中,他们有10%的机会得到500万元,89%的机会得到100万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结果,绝大部分的被试都选择了A赌局。随后,他又设计了C、D两个赌局让这群被试进行选择。在赌局C中,他们有11%的机会得到100万元,89%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而在赌局D,则有10%的机会得到500万元,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结果,绝大部分的被试则选择了D。很显然,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很难对上述实验现象作出良好的解释,因而经济学中将其称为“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
那么,上述的悖论应该如何解释呢?针对这个问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根据前景理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关注某一个财富的参考点。相比于财富的总量,它们会更加重视财富相对于这个参考点的变化。当面临收益时,它们会更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当面临损失时,他们会更倾向于风险爱好。一般来说,一定数量的财富减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将会远大于同等数量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形象地说,丢失100元的痛苦将会远大于得到100元带来的快乐。此外,人们的风险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前期决策结果的影响。具体来说,前期盈利可以使人的风险偏好增强,还可以平滑后期的损失;而前期的损失则加剧了以后亏损的痛苦,风险厌恶程度也相应提高。
运用前景理论,就可以很好地破解阿莱斯悖论:当人们被要求在阿莱斯安排的A、B两个赌局中进行选择时,A赌局中的100万确定收入会被视为是一个参考点。如果他选择了B赌局,那么他就有1%的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这带给他们的痛苦将可能远大于那10%概率获得500万元所带来的快乐。而在C、D两个赌局中,本来他们就有非常大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们将此作为参考点,那么放手一搏赢500万所带来的快乐,将会远高于以一点点的概率得到100万的快乐。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对前景理论后续进行了很多完善。在和塞勒合作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指出了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作用,即当人们拥有某个物品时,他们会非常倾向于持有它。尽管禀赋效应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它却可以解释很多用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在金融市场上,一些股民明知道自己的股票未来走势不会很妙,但却很不愿意将它们抛出,这其实就是禀赋效应的一种体现。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前景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他们将这个理论同时写成了多篇论文,分别投到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期刊。结果,那篇1979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的《前景理论:对风险决策的分析》(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under Risk)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而同期发表在心理学刊物上的几篇论文则应者寥寥。正是这一次墙内开花墙外香促成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后来更多地投身到了经济学界,但尽管如此,他们还仍然将心理学视为自己的主业。或许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前景理论和禀赋效应的一个案例,毕竟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会给他们带来快乐,但可能这并不足以抵消让他们放弃心理学这个旧业所带来的痛苦。
三,框架效应
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指的是人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选择,价值和框架》(Choices,Values,and Frames)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用一个公共卫生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框架效应”。
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正在面临一场疾病的爆发。如果不进行任何干预,这种疾病预计将导致600人死亡。现在,政府已经提出了两种对抗这种疾病的方案。如果采用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用方案B,有1/3的概率会让600人都获救,但有2/3的概率会导致所有患者死亡。在描述完上述设定后,被试被要求选择一个更为喜欢的方案。结果有72%的被试表示他们更喜欢A方案。
然后,他们让另一群被试也考虑类似的选择。他们给出了C、D两个方案。如果采用C方案,将有400人会死亡;而如果采用D方案,则会有1/3的概率让所有人获救,而有2/3的概率导致所有人都死亡。结果,在这群被试中,有78%都表示会选择D方案。
如果我们对上述两组选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给出的选项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表述方式有了不同。在第一组选择中,给出的A方案强调了可以拯救的患者数,这会引起人们更为关注收益中的风险厌恶,这会让他们感觉以A方案确定地拯救200人要比B方案的期望拯救200人要好。而在第二组选择中,对死亡的强调则会唤起人们对损失的风险偏好。他们会认为,与其让400人确定地死去,倒不如尝试一下冒险,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人获救。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后,有很多学者对框架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塞勒。在和约翰逊(Eric Johnson)合作的一项研究中,他在框架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并用它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根据金融学的理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资产组合不断进行配置,当他发现某项资产未来收益堪忧时,就应该及时抛出它们,并将资金配置到更优质的资产上。但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大批股民在经历了股票暴跌后都不会愿意“割肉”并重新配置资产,而更愿意坐等它重新回本。塞勒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因为投资者人为地为不同的资产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心理账户,将它们的盈亏独立地进行了核算。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就会过分关注某个个股的涨跌,而非整个资产组合的收益变化。
学术生涯的晚期
在涉足经济学领域的早期,卡尼曼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人的决策偏差问题上,而在学术生涯的晚期,他则又把关注的焦点重新移回了早年关注的享乐心理学问题,并尝试将这个理论和经济学相结合,从而探索一套基于体验的幸福感(Experienced Well-being)的经济理论。
卡尼曼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人的认知偏差不仅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偏离最优,在一些情况下,人们还会因为错误估计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幸福后果,从而让自己的行为难以达到最优的结果。在2000年的论文中,他指出人们倾向于使用“过渡规则”(TransitionRule)来思考问题,他们对于某个新情况的初始预测通常很准确,但却会把这初始预测错误地用作预测该情况长期影响的代理变量。由此,他们总是会倾向于低估适应带来的效用后果,而夸大生活中的变化所导致的效用变化。
在卡尼曼看来,幸福应该是经济学关注的最终对象,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应该以纠正人们对幸福感知的偏误,引导人们实现幸福的最大化为目标。基于这一理念,他和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len Kruger)一起,建立了一套“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指数包含四级指标体系: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指标体系中都由若干个指标构成。在计算每一级的指数后,再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指数。虽然这个指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GDP之外,用以评估国家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在后续的研究中,卡尼曼围绕着经验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进行了很多工作。根据谷歌学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几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
2011年,卡尼曼出版了《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and Slow)一书。虽然这本书的定位是一部通俗读物,其学术性并不强,但它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学术成就的一个总结。
在这部书中,卡尼曼指出人类的认知系统包含两个部分:系统1和系统2。其中,系统1反应快速、依赖直觉,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而系统2则具有惰性,它的工作就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不过它也更为理性和精确。
在卡尼曼看来,包括启发性偏见、前景效应、框架效应等问题,就是由于人们在决策时太多地依靠系统1而导致的。因而,为了克服它们的干扰,人们就需要在很多时候让思考慢下来,让系统2更好地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曼并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只告诉人们发生了哪些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针对现实中的认知偏差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比如,他提醒人们在决策时,应该要意识到启发性偏见的存在,主动地对这些偏差进行矫正;而对于“事后诸葛亮”问题,他则建议引入一种“事前验尸”(premortem)的思路,在可能的事故发生之前就假设它已经发生,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倒推项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此外,他还告诉人们,这些认知偏差并不完全是有害的。如果善加利用,这些思维捷径其实有助于实施良好的政策。包括桑斯坦在内的很多学者已经将卡尼曼的上述思路用于实践。他们在环境、能源、法律等多个领域都利用了人的认知偏差进行了政策“助推”,从而让政策的执行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在卡尼曼生命的最初十几年,他无疑是不幸的:童年丧父,颠沛流离,忍饥挨饿……或许,正是这些磨难导致了他早期的孤僻和不合群。但是,这些磨难并没有打垮他。虽然现实的世界战火纷飞,但他却从书本和知识中寻求到了宁静。在战争阴霾散去,生活重归于平静之后,他并没有执着于过去留下的创伤,而是选择了最为积极的享乐心理学作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将探究幸福的秘密作为了自己的追求。与特沃斯基结识之后,他又积极地抓住了珍贵的友情,并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创造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毫无疑问,卡尼曼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形容他的一生,恐怕是最为贴切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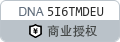
本文经「原本」原创认证,作者经济观察报,访问yuanben.io查询【5I6TMDEU】获取授权信息。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致电:【010-60910566-1260】。
- 原文作者:知识铺
- 原文链接:https://index.zshipu.com/stock001/post/20240406/%E5%BF%83%E7%90%86%E5%AD%A6%E5%AE%B6%E4%B8%B9%E5%B0%BC%E5%B0%94%E5%8D%A1%E5%B0%BC%E6%9B%BC%E7%9A%84%E7%94%9F%E5%B9%B3%E5%92%8C%E5%AD%A6%E6%9C%AF%E8%B4%A1%E7%8C%AE--%E7%9F%A5%E8%AF%86%E9%93%BA/
- 版权声明: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原文链接),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 免责声明:本页面内容均来源于站内编辑发布,部分信息来源互联网,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者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客服进行更改或删除,保证您的合法权益。转载请注明来源,欢迎对文章中的引用来源进行考证,欢迎指出任何有错误或不够清晰的表达。也可以邮件至 sblig@126.com